陈尚君先生治学,以文献、史实考证见长,泰半精力萃于唐诗。搜罗之广博,体例之完善,分析之细密,罕有伦比。近来他取自己相关文字略加简择,都为一编,题名《唐诗求是》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(2018年7月)。捧读后,偶有一隅感发,写出就教高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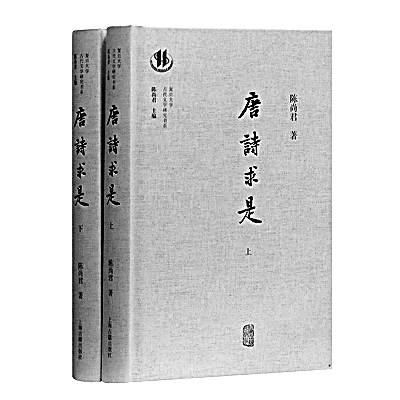
2011年,陈先生发愿凭一己之力,编纂《唐五代诗全编》(以下简称《全编》),斠理至今,蒇事在望,尤为学界翘首以盼的大工程。其面目,从本书可以窥见一二。
进行中的《全编》,包含两大部分:校录文本以外,另列纪事,搜辑、考辨唐五代诗本事,认识多有细化。本事之于研读诗作,有时相当关键。譬如唐中宗景龙二年(708年)至四年,君臣酬唱频繁。赵昌平先生《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》一文论证,七律体制正式定格,即在这一时期,为应制唱和所推动,并考出其中六次确凿时间与作品。唐玄宗时,武平一撰《景龙文馆记》载其事,今佚。贾晋华教授为作辑本(收入所着《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》,后来陶敏先生另有辑本),复参据其他典籍,考得期间君臣文学活动66则,诗367首(不含断句),叙述加详。这次陈先生重辑《记》文,在此基础上,逐日考订酬唱者及存世作品,厘清原委(《〈唐五代诗纪事〉编纂发凡》),想来收获更丰,应有助于七律体式演变研究,步入愈发精确的境地。
当然文本校录,依旧是《全编》工作重心。陈先生从役有年,甘苦备尝,由此总结的若干经验,颇具独到之处。譬如刻下学人,每强调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,文本稳定性有别;他则一再指陈:“今人喜谈写本时代的文本形态,我仅能作部分的赞同”(《大梅法常二偈之流传轨迹》),因为“钞胥固不免手民(按:‘手民’疑当作‘移录’)之误,刻本更难免射利之求”(《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》),两者讹伪“性质、形态或有不同,但结果是一样的”(《唐诗文本论纲》)。见解迥异时流,发人深省。又如目前整理别集的通例,是择一保存作品较完整的版本作底本,在此框架下校正损益;他则指出:其一,唐诗文本流播变异的轨迹各不相侔,整理者有必要“区别对待,每一首诗确定底本和参校本”;其二,今见别集编次,往往历经众手,形成过程曲折,整理者应该不为所缚,尽量恢复较早的文本样貌(《唐诗文本论纲》)。基于这两点,陈先生的处理便与众不同。像许浑诗,罗时进先生《丁卯集笺证》不依傍单一善本,而逐首选定底本,已超出通行做法一头,但目次仍循《全唐诗》之旧。换言之,见及其一而未及其二。陈先生重新编录,“前三卷以乌丝栏诗真迹为底本,其次各卷分别用蜀本、书棚本、元本另见诗为底本,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许诗的初始面貌”(《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》)。他的办法,是区分各版本同原貌距离远近,先取较近者为底本,阙漏处再取其他版本补足。因此,底本常由多个版本缀合而成。张籍、王建、元稹、刘长卿、权德舆、陆龟蒙等家,也本此原则董理。这为唐人别集今校,提供了一条崭新思路。
而最重要一点,是陈先生的目标,不止于写定文本。他说:“前代古籍校勘学更多希望通过文本校勘,改正文本流传中的讹误,写定一个错误较少的文本,但对唐诗来说,仅此远远不够,我近年更多认为要把唐诗文本形成、刊布、流传中的多歧面貌充分地揭示出来,为后人的研究展开立体空间。”(《唐诗文本论纲》)一方面,“唐诗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”(自序)还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仅此一端,已然裨益学者匪浅。譬如皮日休与陆龟蒙等人唱和的《松陵集》,原题起初三次,陆氏皆称前者“袭美先辈”,以下则径称“袭美”,间或称其“鹿门子”。两人关系由疏而密之迹,班班可考。此类原始信息,经《甫里先生文集》《全唐诗》等书改题后,多被遮蔽,足见文本原貌之珍贵(《唐诗的原题、改题和拟题》)。另一方面,陈先生悬鹄更高,又力图把唐诗文本传讹的经过,分层次揭示出来。为此批评一套李白集新注,校勘虽认真,却“没有就每首诗的文本来源作详尽记录”(《郁贤皓先生〈李太白全集校注〉述评》)。未来《全编》校勘记,必定空前翔实,不妨视作一部特别的唐诗文本变形记。这些记录,确能为研讨拓出一方“立体空间”。譬如从敦煌卷子、吐鲁番文书、长沙窑瓷器题诗、山西长治墓志志盖题诗,足以领略唐诗在民间流布的特点。百姓喜闻乐见之作,表达的都是劝学、惜时、送别、怀人、思乡、羡官羡富等世俗情趣;意思取其简单,语言取其浅易,故着名诗人,只有王维、白居易、刘长卿多次入选,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李贺、杜牧、李商隐等人几无踪影;就文本言,随意删节、拼接、改写、另题作者,殆成常态。不过同时,陈先生也提醒:“民间对诗歌的最基本要求是通俗易懂,一流大家的追求则在诗歌史上的开拓创造,取径不同,结果自异,不能因此而认为杜甫等人在唐代缺乏影响力。”(《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》)观其《杜诗早期流传考》《李杜齐名之形成》等文,自不难了然。唐诗在文化阶层与民间平行传播,所展现的动态景象,即是“立体空间”之一表现。
由于唐诗异文来源纷繁,如何梳理次第、解释成因,有待学界共同探索。在陈先生看来,异文若宋代已有之,极可能为诗人自改稿。譬如贺知章《晓发》题下,有五言八句一首,又有五言四句一首,割截前篇诗句,颠倒以成文。陈先生认为:“从宋初即有二本之流传,显非传误所致,应该是诗人所作即有繁简二本。”(《贺知章的文学世界》)这大约出自他对宋本的信任:“尽管宋人确有主观改诗的个案,但无论李、杜、韩、柳诸集,还是《文苑英华》《乐府诗集》等总集,宋人校记的分寸把握是很严格的,很少如明人那样为射利而随意改变窜乱。”(《近期三种杜诗全注本的评价》)然而唐集入宋前状况,多半云遮雾障;宋人“主观改诗”,也非绝无可能。宋本异文是否即诗人亲笔,似乎不宜遽定。举《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》为例。文中描述,李白集宋本有两个系统,今犹依稀可窥:一为乐史所编,现存南宋咸淳刻本源出于此;一为宋敏求所编,晏知止刊印(按:晏刻本实为宋敏求本再经曾巩编年后的新本,参看万曼《唐集叙录》),现存蜀刻本两种源出于此。陈先生执敦煌卷子伯2567所存李白诗,与蜀本相较。他推测敦煌本“当出自李白的初稿,重要证据是诸诗诗题提供了一些有关各诗写作时不为人知的细节”,理由坚实。如此,则蜀本异文为事后修订。问题在于,修订者是否李白本人?譬如敦煌本《赠赵四》,蜀本改题《赠友人三首》其二,文字歧异甚夥,他以为“宋本所收显属写定本”。可是前者“防身同急难,挂心白刃端”两句,后者改为“持此愿投赠,与君同急难”。30多年前,黄永武先生便指出全诗押真、寒、先三韵,敦煌本转韵处,出句皆押新韵。这两句转入寒韵,而改本出句不押,“破坏了原作在音响方面暗藏的秘密”(《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[上]》,收入所着《敦煌的唐诗》)。字句妍媸,言人人殊,且改稿也未必优于初稿。但倘说李白润色时,连原先的音节规律都抛之脑后,令人不能无疑。又如敦煌本《惜罇空》,蜀本改题《将进酒》;前者“岑夫子,丹丘生。与君歌一曲,请君为我倾”四句,后者在“丹丘生”下加“进酒君莫停”一句,又末句改为“请君为我倾耳听”(末句陈先生未与蜀本比较)。黄永武先生指出,两处改动当在一时,因为“生”字在庚韵,“倾”字在清韵,唐代庚、清通押;新添句“停”字则在青韵,宋初庚、清、青三韵不通押,末句只得加“耳听”二字,以同在青韵的“听”字与“停”相押。他从而推论:“本诗的改动是在宋代初年”(《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[下]》)。这两例至少说明,蜀本异文出于谁人笔下,判断尚须谨慎。周勋初先生尝言:“宋刻李诗,不管是蜀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,抑或景宋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,因为已经后人之手,上距唐代已远,所以还不能算是接近李诗原貌的首选材料。”(《李白诗原貌之考索》)他的意见值得重视。
以上仅围绕唐诗文本校写一事,加以申述,实则《唐诗求是》于此之外,又收入不少诗人行实、文献形态方面的考论,同样胜义纷披,愧未能一一阐扬。读者欲观其内容的千汇万状,仍当求之本书。








